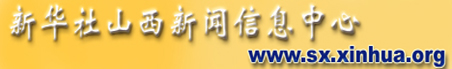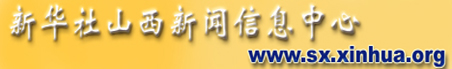|
新华网山西频道7月27日电 6月22日的一起爆炸,使37名矿工惨死井下,也使五台山北麓的繁峙县一夜成名。
拥有丰富的黄金资源,而本身又是国家级贫困县,这种现象让许多外人困惑不解。
极少数人的富裕衬托了绝大多数人的贫穷。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这一利益格局愈发明显也愈发错综复杂。
靠山吃山、农民进城、国企困顿、穷县脱贫是繁峙转型期的主要特点,由此引发的私挖滥采、治安恶化、道德沦丧、矿难频发只是表面的现象……
单纯指责矿难,在某种意义上价值不大,发掘矿难的背后,或许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老侉儿”走后
繁峙县与河北省交界,“老侉儿”本是繁峙人对河北人的称呼,但现在这个词用意广泛,只要不是山西人,一律叫“老侉儿”。
丰富的金铁资源,使繁峙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成为外来人口汇聚的地方;尤其是砂河镇北边的义兴寨金矿区,更聚集着好几万淘金的“老侉儿”,其中多以陕西、四川、湖北人为主。
今年6月22日,省义兴寨金矿的协议探矿区0号脉发生爆炸,导致37名外省矿工死亡,事件一出,全国震惊。
事后,矿主意欲“私了”此事,从而隐瞒真相,转移尸体、焚尸灭迹,最后畏罪潜逃,使这起矿难事故彻底转性,演变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刑事案件。
接踵而来的矿业秩序大整顿,引发了该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民工潮”。从6月30日到7月6日的一周内,共有近两万“老侉儿”被紧急疏散后返乡。
铁路、公路等运输部门为此饱赚了一笔。砂河镇汽车站和五台山火车站日日人满为患,车车严重超载。
本报记者到达繁峙时,已是7月11日。一路上,“依维柯”的车主不停地向乘客诉苦,说“近几日生意惨淡,天天赔钱,把前几天赚得全吐了出来”。
“老侉儿”走后,感到生活压力的不仅是依维柯车主。砂河镇镇长侯权介绍说“砂河镇各行各业的总销售量都下降了60%左右”。
砂河镇位于繁峙县正中央,108国道和京原铁路从此穿过。历史上这里曾是繁峙县县政府所在地。凭借区位优势,这里成为繁峙县乃至北方的商业重镇。
20世纪80年代后期,省义兴寨金矿开始建设;同时,义兴寨、金山铺、伯强等乡的金矿区开始大规模私挖滥采,吸引了无数淘金的“老侉儿”,也造就了一大批本地的“金老板”,砂河镇日益成为涉金产业的生活区和总后方,附近山上“老侉儿”的吃住行及采金行业的设备材料购置、修理均发生在此地。
侯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砂河附近共有两万左右在金矿打工的“老侉儿”,平均工资在1500元左右,按每人每月消费500元计算,消费总额就是1.2亿元,就这还不算挥金如土的“金老板”们。
繁峙县2001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过区区两亿元,“老侉儿”在其中占绝对份额。
繁峙一年的用电量为1.2亿度,“涉金的约占一半”;在经济落后的忻州,繁峙经济约排倒数第二,但用电量却排在前三名。
据说砂河镇每日要宰杀200斤的猪200头以上,主要供应产金的义兴寨和浪涧山(位于金山铺乡)。 “6·22”矿难使这一切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的砂河镇百业萧条,许多饭店、商铺已贴出了“转让出租”的告示。
梦想中的“金山”
义兴寨,“老侉儿”梦想中的“金山”。繁峙县两山南北对峙,县城和砂河镇位于其中的滹沱河谷地。从砂河镇乘车往北走10公里山路,便是大名远扬的义兴寨金矿区。
义兴寨村原是义兴寨乡、镇府驻地。乡镇撤并后,这里被并入砂河镇管辖。 义兴寨名气很大,太原发往繁峙的“依维柯”大多上书“太原———义兴寨”,中间的小横上写着“繁峙、砂河”。
繁峙县共有8个有证金矿,其中义兴寨矿区占了四个,分别是省义兴寨金矿,集体所有的县义兴寨金矿及股份制的义联金矿和县金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此外,就是那遍布山间、不计其数的民采无证小矿,即私挖滥采。
有人告诉记者,义兴寨有不少村民参与私挖滥采,而井口就在自家院内。 同行的本地向导说义兴寨以前非常穷,20世纪80年代后期“靠山吃山”,不少村民靠私挖滥采发了财,现在这里“富得流油”。
此次出事的松涧沟0号脉属省义兴寨金矿管辖,位于矿山东部,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2公里的山沟,共有33个以采代探的硐口。爆炸的矿井是1号,硐主叫王全全,是义兴寨村民,至今在逃,公安部门悬红三万元捉拿。
现在的松涧沟已回到了农耕时代的宁静。无数的断壁残垣和生活垃圾显示出这里往日的热闹。几千名“老 侉儿”已被政府驱逐回乡,1242间临时建筑被拆除,几十个矿井也被执法部门炸毁。
爆炸的矿井因被硐主和工头们填埋而破坏,爆炸原因至今没有公布;爆炸现场已被公安部门封锁,“非专业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从附近山坡上往下眺望,爆炸现场一片繁忙,来自大同的矿山救援队正对出事矿井进行紧张的发掘工作。
一群干部模样的值班人员用“无可奉告”打发了记者。
松涧沟里原有一个松涧村,前几年集体迁到了沟外的沿口河河畔,改名叫下河湾村。“老侉儿”走后,村民们集资在松涧沟入口处重建了一座关帝庙。7月13日下午,记者看到泥塑的关老爷脸还未被漆红,绘漆的范师傅说该庙“投资了三五万元”。
下河湾的村民听说记者来采访,立即聚集了几十人,大家七嘴八舌述说着“老侉儿”的故事。
“矿上不要本地人干活,只要老侉儿”,原因是“本地人死了要花十几万元,而老侉儿只要两三万元”。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把农电给了矿山用,搞得电压只有110伏,连电视也不能看,现在好了”。在村民王梁海的院里,存放着三台空压机、三台发电机,其中几台非常新,大家说是某个硐主存放的设备。
村里的房屋很破烂,看上去并不富裕;但家家的门窗都安装着铁护栏,据说是怕“老侉儿抢钱”。下河湾的众村民呼吁政府把松涧沟的30几个竖井填死,“怕小孩和牲口掉进去,几百米深,掉下去根本没救”。
顺下河湾村边的沿口河往下游走200米,有两座规模不小的选矿厂,其中一个厂子的房屋尚未封顶,院中堆放着十几台大型的发电机、空压机,全是采矿用的设备,看门人说:“一台就得几十万元”。据说这里的老板叫杨文宽,也开着金矿,是义兴寨村民。
对“老侉儿”的感觉,义兴寨村民完全不同于依靠农业的下河湾村民。这里的1000多村民基本不种地,全部依靠矿山,或私挖滥采,或为“老侉儿”提供衣食住行服务。
一个小小的村子,竟开有几十家饭店,至于干洗店、发廊等服务设施更是鳞次栉比;记者在街头漫步,还发现此处开设有三家移动和联通的代办点。
义兴寨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小广告,有些药店居然打出“早孕测试、性保健品”的招牌。在民风质朴的山区,这种场景令人诧异。
但现在,99%的店铺已铁锁高挂,关门停业。
村支部副书记刘文生带记者去了在逃的硐主王全全家。王全全的家人全部不知去向,只留有一个自称是“远房亲戚”的小姑娘看门。
王全全的邻居是王四女。据其讲,她借了一万多元盖了40间简易房,平时租给陕西平利县的一个采金队住,“有200多老侉儿,一月房租能收四五千元”。
王四女的简易房里,至今还住着许多不肯离开的“老侉儿”。陕西镇安县的肖剑辉和平利县的孙玉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们告诉记者,陕南的老家位于秦巴山区,生活比繁峙还苦,种地的收入还不够交各种摊派,“交不起乡干部就去家里搬东西”,无奈只得出门打工,听同乡说繁峙金矿挺赚钱,就来到了山西。
“6·22”矿难中遇难的37人均是来自陕西南部安康地区贫困山区的农民。
他们大都是淳朴善良的农民,这是和许多“老侉儿”交谈后记者最深刻的感受;由于缺乏特殊劳动技能,只能靠体力吃饭,到矿山打工也许是最无奈的选择。
“金老板”的传说
繁峙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丰富的金矿资源并未给县财政带来多少好处,原因是黄金免增值税;加之各有证金矿受私挖滥采影响普遍效益不佳,所得税也寥寥无几。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进行私挖滥采的“金老板”们。他们的极度富裕掩盖了繁峙县大部分百姓的极度贫穷。
砂河镇镇长侯权介绍说“金老板都是当地农民”,其中义兴寨、砂河镇和代堡村金老板最多。
侯认为“当地老板仗的是本地人优势,而外地老板仗的是劳动力优势,双方一起投资,一起受益”,而“外地的工头赚得最多”。
繁峙县历史上就有民间采金的传统。其县志记载:“早在唐代,义兴寨的山脚下就开采过黄金。东西两山有采金的古洞,洞内有遗留的骸骨、锤钻、唐代开元钱币和锤钻凿掘印痕”。
改革开放后,当地农民“靠山吃山”,纷纷打起了金矿的主意。
一个大背景值得一提: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掌握国家地质资料的地质勘探部门转换机制,变成了国家不拨一分经费的事业单位,地质人才大量外流;而私挖滥采正起步于那个时候,这种巧合绝非偶然。
据介绍,打一个百米深的矿硐至少投资百万元,没有“高人”指点,这个硐很可能是个不出金矿石的“干硐”,这种风险无人敢冒。
私挖滥采有了民间基础,使得整顿工作陷入困境。据介绍,义兴案寨地区已进行了“13次整顿”,出现了“14次回潮”。“金老板”和“老侉儿”在地形复杂的各山沟和政府执法部门展开了“游击战”、“地道战”,使繁峙县政府头疼不已。
中国的农民是聪明的。在收益日薄的种地和利润奇厚的采金间,他们很容易作出了选择。
谋生的艰难和对财富的渴望使法律受到蔑视。
一个一再要求隐去姓名的乡镇干部向记者透露了部分“金老板”发家的秘密。“一个矿硐投资百万元,普通人根本投资不起,起初村民们采取的办法是集体入股,股份最大的当地人担当硐主”。
“像代堡村,大多数家庭在民采矿中拥有股份”。
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原始积累后,繁峙县出现了大批的“金老板”,他们也拥有了三五个人投资一个矿硐的经济实力。
“6·22”矿难使殷山、王全全、石新全、苏仕滨几个“金老板”和工头闻名天下。纷纷外逃后不久,殷山就被抓获,“据说心脏病突然发作,导致审讯工作无法进行”。
这些“金老板”在金矿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至今是个谜,记者只听到一些模糊的传说。
和省义兴寨金矿签订了对0号脉进行探矿协议的殷山是个较大的“金老板”,其经济实力众说不一,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千万元左右”。
殷山的“座骑”是一辆牌号为“晋H70007”的白色“尼桑V6”,已被扣在了砂河镇派出所,和周围破烂的“2020”警车形成鲜明对比。
砂河镇镇长侯权说:“殷山是个很普通的农民,生活没什么品位,有钱也不会花”,“抽烟就是个‘国宾’,当老板还自己下井”。
许多人评价殷山是个“土老财”。几经波折,记者在砂河镇西关村找见了殷山的女儿殷冬梅和小儿子殷向东。殷冬梅向记者介绍了父亲的部分情况。
殷山原是繁峙磷肥厂职工,企业效益不好后自谋出路。在学校里卖过挂面,开过面包车,跑过出租车,为生计而吃尽了苦头。 殷山的前期故事是中国国企下岗职工在社会上艰难打拼的一个缩影。
殷山发家于1992年,转机就是介入了“金矿开采”。日渐富裕的殷山在繁峙砂河镇买下一家“东关旅社”,在太原“佳地花园”拥有了50万的私产,并且把小儿子送到太原南洋国际学校念书。
殷山在松涧沟的探矿承包费一年是110万元。殷冬梅讲“父亲只有5万元,李小勇和杨海龙股份最大,杨海龙有60万元”。
杨海龙,绰号“大海龙”,砂河镇代堡村人,是远近闻名的“金老板”。
殷冬梅并不懂“金矿不允许民采”的法律规定。
殷冬梅认为父亲“没什么文化,连法人代表都不知什么意思,在矿上主要搞管理,其实是个小股东,说穿了是个跑腿的”。
殷山的小儿子殷向东说“在南洋国际学校上学的繁峙老乡有七八十个,父母都是开金矿的”。
殷山又把0号脉分包给33个硐主开采,王全全是其中之一。
在义兴寨,记者听说硐主王全全的股份只有两万元,“大老板是陕西人和江苏人”。
“6·22”矿难后,繁峙的“金老板”们纷纷外出躲避风头。记者寻遍义兴寨和代堡村,也未见到一个。 (山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