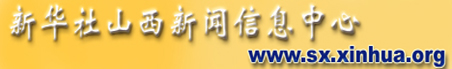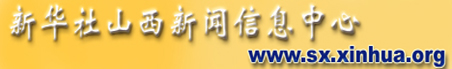|
新华网山西频道7月27日电 “瞒报”的土壤
矿难并不稀奇。今年上半年令人目不暇接的空难、矿难已让人们习惯了这类新闻。
繁峙“6·22”矿难之所以引起新闻大炒作,是因为“隐瞒真相、焚尸灭迹”。
县里一位新闻干事介绍说,矿难发生后,前来采访的记者有100多人,“仅中央电视台就来了四拨”,加上众多的专案组成员,导致砂河镇的各大旅店、宾馆人满为患,有的记者不得不五六个人挤在一个标准间。
对媒体上炒成一团的“隐瞒真相、焚尸灭迹”,义兴寨的老百姓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镇定。一位村民说“矿上一直这样干,没什么大惊小怪”。
一位县领导认为“事故具有隐蔽性,工人又有很强的分散性,使矿主私了成了习惯”。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干部都认为“瞒报有其生长的土壤,决不是地方政府瞒报”。
出了矿难后,矿主决不愿让地方政府知道,因为怕地方政府停产整顿、炸毁矿硐,那样损失更大;而遇难者家属也愿意“私了”,因为“私了”的价格一般比“公了”高。
至于焚尸灭迹更不是稀罕事。出了矿难后,将尸体运往忻州火葬场火化要花几千元费用,遇难者家属一般不愿出这笔钱。花上几百元就地焚烧是“非常便宜的火化方式”。
砂河镇镇长侯权介绍了“6·22”矿难被县里知晓的经过。
6月22日下午,已离职的原义兴寨乡副书记王焕生在义兴寨村闲逛,发现义兴寨的某街头小门诊正在抢救受伤民工;又听旁边有人议论“松涧沟爆炸了”,就给砂河镇书记原国清打电话,原国清随后向县长、县委书记汇报了此事。
随后,县里又向忻州市汇报了此事。
当时正是个周六,县领导均在县里研究乡镇撤并后的副职人选。接报后,书记、县长立即带人上山检查。殷山等人已伪装好现场,信誓旦旦地向县领导汇报“死两人、伤四人,其他人安全撤离”的谎言。
“如果不是王焕生,县里不可能马上知道出了事,殷山等人就没打算报。”
侯权认为“如果那天王焕生没报,又没人举报,县里反倒没事;县里知道此事后却被矿主蒙蔽,反倒让县里很被动。后来媒体怀疑县里参与瞒报,县里是有嘴讲不清”。
为侯权的话提供佐证的是义兴寨开门诊的王俊利。王是义兴寨人,大同医专毕业后回村开了诊所。王告诉记者,6月22日下午山上拉下来一个“老侉儿”,“过度惊吓引起惊厥、神志不清”,王为该矿工输了一晚上液,第二天该矿工清醒后,说要“上山找老板要药费”,结果一去不返,欠下200多元药费至今未还。
该矿工被抬下山时未穿鞋,王还为其买了一双布鞋,邻居嘲笑王俊利“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繁峙采访期间,又闻浪涧山矿区发现两具干尸,和这次矿难没有任何关系,“一看就是私了的”。
举报者的故事
胡江,陕西省旬阳县民工。因向国家安监局和媒体举报“6·22”矿难,被众多媒体誉为“英雄”。
此次矿难中,胡自称有三位亲人在井下遇难。因未能辨认出尸体,胡在繁峙等候公安部的DNA鉴定结果,并接受了本报采访。
胡江说此次他“逃了一命”,原来他也在王全全硐里干活;后来去了另一个硐,老板叫刘峰,是矿上的大老板刘胜耀的哥哥。
胡江说“王全全硐的工程股共有12股,刘峰也有份,还有个陕西股东叫吴胜贵,负责安全。”
某媒体报道说,出事后胡江等家属被刘胜耀等人软禁,这和胡江的话有些矛盾。
胡江说,6月24日他在砂河镇碰见了吴胜贵,还和吴吃了一顿米线。吃完饭后胡问吴“这个事情咋弄?”并说自己知道死了多少人;吴说“不要胡说,死了两个,伤了四个”;胡便反驳说“我亲眼看到的,和我弟弟一起来的六个全死了”,吴没吭气就走了。
记者询问胡江为什么6月22日到24日都不向地方政府举报或报警,胡不知所云。
有人推测“胡江当时想问矿主多要些钱,达不到目的才举报”。
这样揣测死者家属未免有些不人道。但采访时记者的确听说部分家属毫无悲痛,只是一味地和政府讨价还价;更有的已和矿主签了“私了协议”的家属找上门来,“要求补上和政府所订5.5万元的差价”;还有的家庭听不见哭声,只有一片争夺抚恤金的吵骂……
在市场经济中,金钱越来越影响了人际关系。“金老板”和矿工们的道德滑坡同样值得重视。
省直矿山的尴尬
山西省义兴寨金矿是省直属的一座国有中型黄金矿山,1986年破土动工,1991年正式投入生产。其设计年产黄金1.2万两(375公斤)。
不到实地看一看,不知省直矿山的生存艰难,同行的新华社记者说其面貌“像个乡镇企业”。
省义兴寨金矿的一份材料中提到:“自1991年正式投产运营以来,一直饱涵着坎坷与艰辛。先是基建阶段造成的先天不足,一直难以达产,再加上后来矿区内民采活动的大肆干扰破坏和生产经营封闭落后的传统管理模式,使企业顾此失彼,始终走不上正规发展之路。尤其是1996-1998年这3年间矿山整个开采系统遭到民采和越界开采的严重破坏,井下各中段的采场已大部分被民采占领,仅1150中段以下损失矿量就达174495吨,金属量1408公斤,到1998年5月,矿山终因内部资金困难,资不抵债,无力与非法采金抗衡而被迫停产”。
有资料表明,省金矿总负债7000万元,而其固定资产不足4000万元,早已资不抵债。县里一位干部说:“省里一直视之为包袱,想把该矿给了县里;繁峙县是个穷县,背不起这个包袱,所以一直不敢要”。
1998年,韩宝庭走马上任省金矿矿长,开始严厉打击私采和越界开采。结果他的车被砸坏,还有人往该矿办公楼上扔了两个炸药包。
现任矿长杨林河据说也是“强硬派”。结果去年矿山的高压电杆被炸坏,几百名矿工被困井下,幸亏抢救及时,才未酿成大祸。
很难解释省金矿的现有格局是否是一种相妥协的结果:省金矿成立了“生产二部”,开采南斜井附近的11个非法井口,据说二部实行股份制,股东主要是繁峙的“金老板”;省金矿所属6号脉分布着13个非法矿硐,13个“金老板”以“作业组”的名义和省金矿签了承包协议;省金矿所属0号脉和殷山签订了探矿协议,而事实是以采代探;就连省金矿的主井现在也包给了一名叫金国忠的陕西“金老板”生产,省矿正式工无一下井,其利益分配模式无人透露……
“6·22”矿难发生在0号脉。暴露的问题是殷山个人既无探矿资格,又无采矿资格,如何和省金矿签订了协议?二是以包代管,安全规章形同虚设,“金老板”们急于采金,完全不顾矿工死活。这是省金矿各矿点存在的普遍问题。
由于此事很敏感,矿上职工拒绝透露其它情况。
有人说,“6·22”矿难是好事,大乱之后有大治,但愿如此。
贫困县的挣扎
繁峙县的金矿只富了极少数“金老板”,而繁峙县的大多数百姓尚未脱贫。
年产黄金2.7万两的“黄金万两县”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让许多外人困惑不解。
繁峙县的县情用12个字可以概括,即“资源富县、财政穷县、秩序乱县”。
繁峙县的矿产资源多得令人妒嫉。其生铁探明储量为2.92亿吨,占忻州市储量的22.3%,黄金储量19.2吨,是全省黄金储量最多的县。
而繁峙县的财政收入令人叹息。“九五”期间,其财政收入一直未突破3500万大关;而支出却双倍于财政收入,年年靠上级拨款弥补差额。
造成这种奇怪局面的就是经济秩序混乱、私挖滥采猖獗、税费流失严重,年年开展矿山秩序大整顿,使地方政府开支剧增,疲于奔命却又收效甚微。
为扭转被动局面,县里确定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治乱”,确立了税收秩序、环境污染、矿业秩序、市场准入、安全生产等8个重点整治内容。
为整合县里的黄金和生铁产业,去年繁峙县成立了黄金开发服务中心和生铁服务开发中心,将两大支柱产业统一管理,其重点是防止税费流失。
这项工作的确卓有成效。2001年,繁峙县财政收入达到4024万元,比2000年增长15.7%。
而农业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灾,去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611元,比2000年的1129元减少了500多元。
繁峙县的农业人口近21万,占总人口24万的近90%,脱贫依然是繁峙县的中心任务。
除了脱贫,繁峙县还有一些棘手的工作,其中最大的一项就是打击私挖滥采。民采的特点是“采的资源是国家的,挣下钱是自己的,有了麻烦是政府的”,这次“6·22”矿难让这一特点形象地展示出来。
据估计,为处理这次矿难,繁峙县已花费了各种费用数百万元。由于省义兴寨金矿账上只有几十元,而各矿主被查封的账户不过2万多元,这笔开支县里只好先行垫付。所有的人都在为后半年的日子发愁,大家心里很清楚,“今年后半年县里绝对发不了工资”。
整顿矿业秩序,使全县的金矿、铁矿被关闭,恢复生产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三大支柱产业只剩下粉丝支撑,财政收入计划成为空谈。有人预计这次矿难的长远损失将上亿,“繁峙5年别想翻身”。
多年的私挖滥采更给环境带来了灾难。土法采金排泄大量的水银和剧毒氰化物,使义兴寨附近的沿口河和龙山水库成为“死水”,水里“连个蝌蚪也活不了,更不用说鱼虾”。“松涧沟没有一棵松,浪涧山不见一个浪”,治理积重难返的环境污染,成为财力捉襟见肘的县政府的一大难题。
在繁峙采访期间,全体干部又开始挨山挨沟排查缉毒。这种由贫困引发的农民违法行为,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据了解,该县每年都有数十万资金用于缉毒。
就在前几天,《忻州日报》刊登了繁峙县上半年所取得的骄人经济成绩,其财政收入上半年完成2657万元,同比增长24.39%;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矿难,把这仅有的喜气冲得一干二净。
比矿难更可怕的
和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样,繁峙县也在经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痛苦转型。这场矿难表现出的民工跨省流动、血汗工厂、道德沦丧、矿山无序开采等问题,无一不是转型期的产物。
而令人担忧的是,当计划经济的治理权威和管理体系崩溃后,我们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面对贫富分化、失业剧增、农民进城、犯罪升级等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许多地方政府束手无策。
更为可怕的是,基层由于经费紧张,正常的运转机能已经部分失灵。
以治安为例。繁峙县公安局一年正常运转需经费220万元,而现在只能保障40万元,其恶果是“有警不能出,抓大案放小案”。一个笑话是繁峙县10个基层派出所只有两个有电话,还是只能接不能打的“欠费机”。
矿管、劳动等部门无一不被经费困扰。连饭也吃不饱,如何让基层干部职工安心工作?
频发的矿难,正是整个社会在某个运转环节失灵的讯号。 (山西晚报)
|